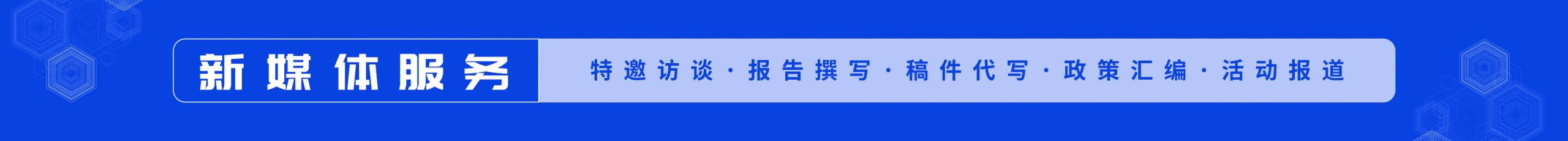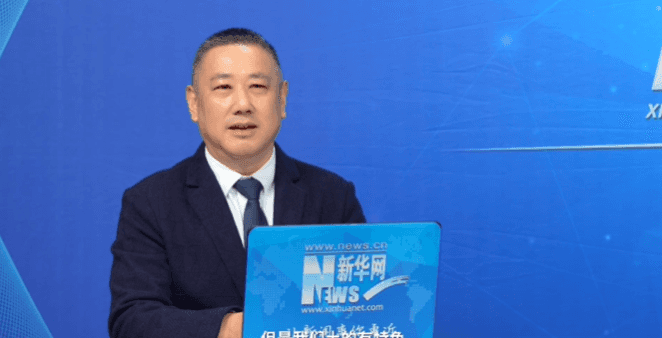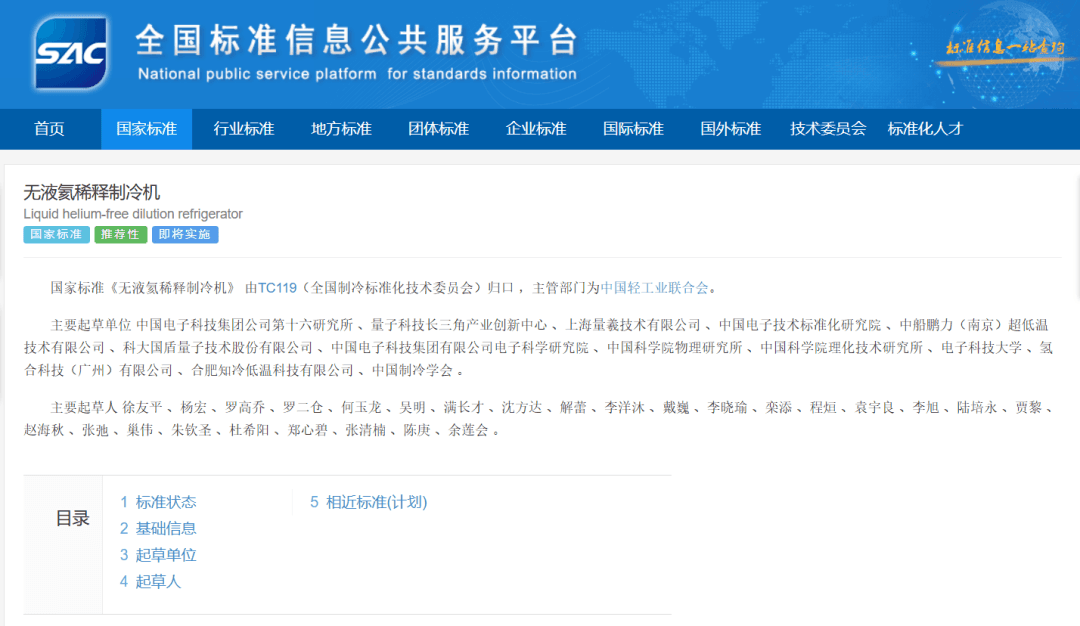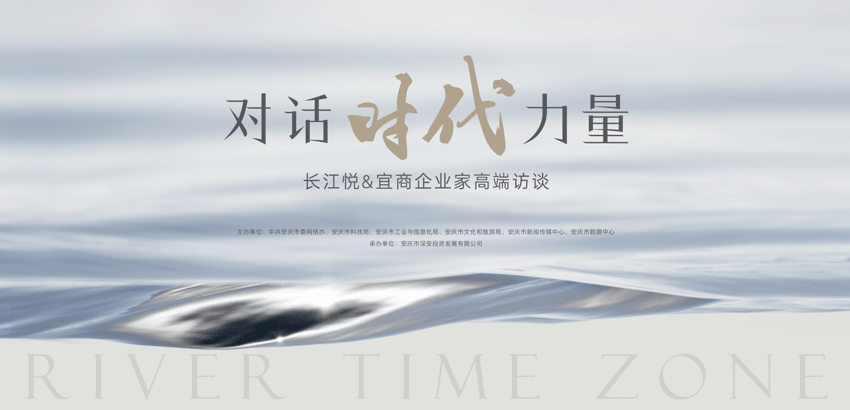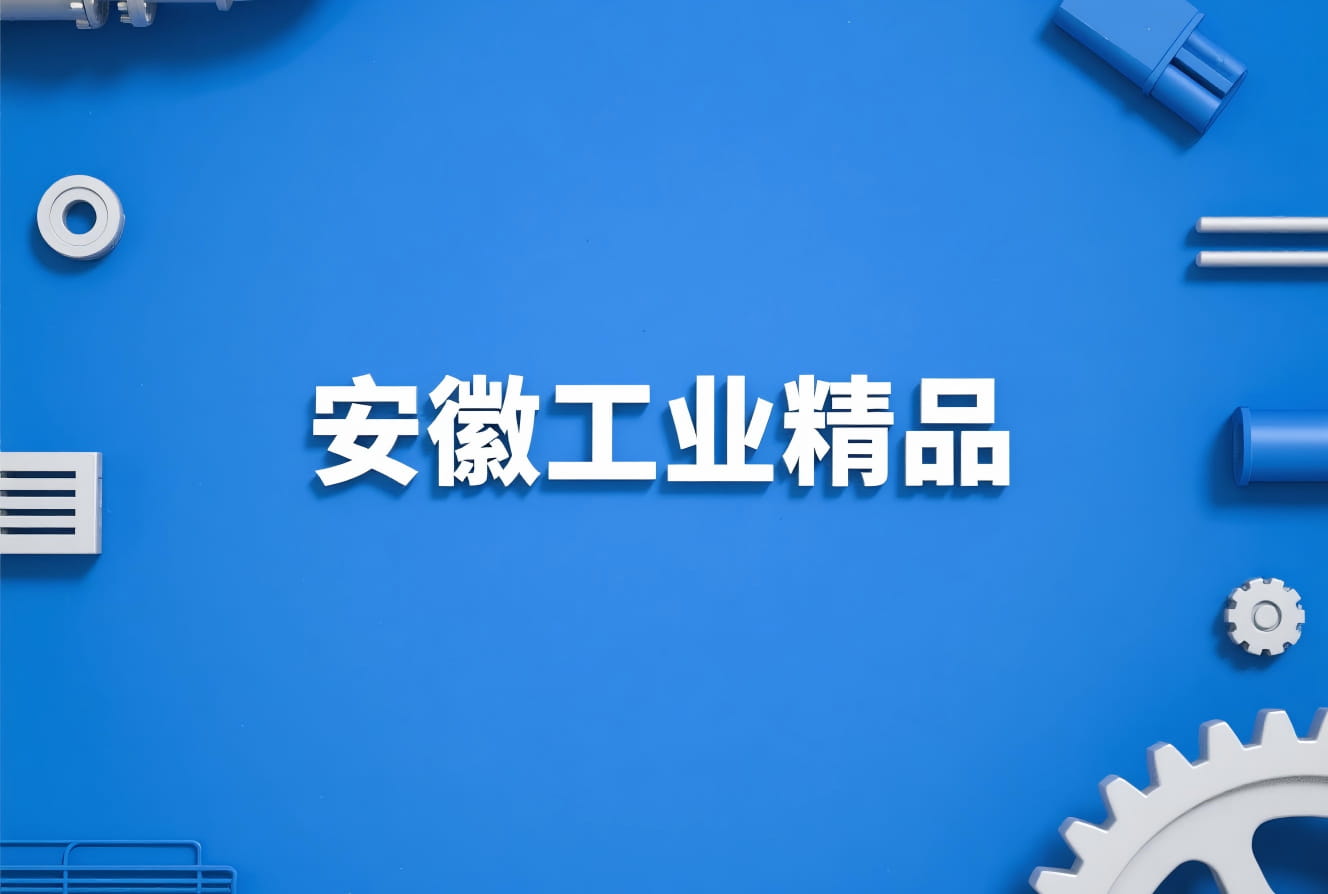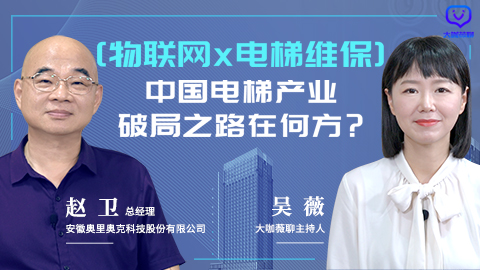专访|安徽环球文旅集团徐华玉:我给自己的定位是:从业40年的旅游业“新”兵
前言
徐华玉,安徽环球文旅集团总裁,高峰时期年营收10个多亿,一个驰骋旅游行业40年的前辈却说自己是新旅游时代的新兵。从平台+创客模式到未来3年的发展战略和组织调整,还有亲子游、老年游、入境游领先于行业的早早布局,他对旅游行业的未来做了很多思考和尝试。
请您介绍一下安徽环球文旅集团
徐华玉:我们环球文旅成立于2003年7月,今年将迎来22周年。
目前公司设有六大事业群:一是面向C端客户服务的休闲度假事业群;二是专注为机构客户提供定制旅行的定制旅行事业群;三是针对3~16岁未成年人的品牌“行知学堂”;四是专注于老年及康养旅游的“老顽童俱乐部”;五是负责安徽目的地运营的业务,在传统地接基础上拓展了更广范畴;最后是融合发展事业群,涵盖文化传播、会议、展览、培训等相关业务。这六大板块共同构成了我们当前的主要业务布局。
最高峰的时候营收多少?
徐华玉:最高峰应该说是2019年,那年我们做到了十多个亿。
最低谷的话,刨去创业期不算——毕竟创业期还在高峰之前——最低是在疫情期间,尤其是2022年,那一年差不多只做了不到5,000万。
整体今年的经营情况怎么样?
徐华玉:今年所谓的大旺季,严格来讲,现在对旅行社已经不太适用了。现在其实都不能叫“黄金周”了,大家可能也有感觉,以前黄金周满山遍野都是导游旗,现在几乎看不到了。这意味着黄金周反而成了旅行社的淡季,基本上那段时间生意很少。我们现在更多是把重心放在日常的服务上。
今年整体比去年略有增长,但增长不到10%。当然,这个增长也不完全代表一种趋势,或者我们有多大改进,可能也包含了不少市场的机遇和机会在里面。
你们今年有什么重大项目吗?
徐华玉:从我们今年来看,整体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,如果非要说有的话,我想第一个是在服务上。我们一直在持续改进——过去很多旅行社的服务或产品非常刚性,而现在我们努力做成柔性的服务,真正去做到以游客为中心、以用户为中心。过去这方面可能更多是个口号,很难落地,但今年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和进步。
尤其是到年底之前,公司的企业文化还会进一步梳理,把这些理念标准化,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规范里,真正做到以创造价值为中心、以客户为导向、以结果为导向。
上次去您公司的时候,看过很多细分品牌,这是不是您提到的平台+创客的业务模式?
徐华玉:品牌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,是慢慢累积出来的。我们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搭平台而做平台,而是看到不同群体有不同需求,就逐一为这些需求创立了品牌。比如2004年,公司成立才一年,我们就注册了“行知学堂”。那时候我就觉得,不管社会怎么发展,孩子是一个独立群体,他们的需求和成人完全不同,所以需要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服务部门去对待。
再到2005年,我们主要为老干部提供服务,在安徽省委大院里面设了一个营业部。很多大院里的老同志愿意跟我们出去玩,我想这些老年群体和普通年轻人也不一样,于是又注册了“老顽童俱乐部”,直接把点设在省委老大院里面。这两个品牌都做得比较早。
回头看,我们公司能活到今天,也希望未来再走30年,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一切从用户角度出发。
后来我们又逐步成立了会展公司、文化传播公司等等,根据不同业务类型慢慢把架构垒起来了。但垒起来之后,各业务都很独立,过于独立就导致内部很难协同。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,如果全是松散状态,那就会出现“1+1+1+1+1未必等于10”的问题。
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公共服务体系,就像创新中心这样——公司搭一个平台、做一个孵化器,让内部创客能在里面自由、健康地生长。于是公司在2017年推动了一次大改革,把传统科层制、金字塔式的结构转变成扁平化的“平台+创客”模式,这也是学习了海尔的经验。我们把层级打平,实现去中心化、扁平化,同时调整前后台关系:前台以客户为中心,后台以前台为中心,从权力部门转变为支撑部门。
现在我们又进一步深化,把前后台细分为“前台、中台、后台”。前台就像华为说的,是打仗的——业务、营销或销售部门;中台是提供弹药的支援部门;后台则负责公司战略和底座支撑。通过这种“三台”模式,我们希望孵化出更多创客。比如老顽童和行知学堂里面,未来还可能裂变出两三个子品牌——假如行知学堂里某块业务做得特别好,比如“行政夏令营”,就可能单独孵化成品牌,研学旅行、亲子旅游也可以这样逐步裂变。这就是我们想做的管理模式:平台加创客。
您觉得中老年旅游和其他旅游业务有什么典型的不同?
徐华玉:中老年业务和传统业务的对比,我想可以分几个阶段来看。
过去主要是以组团为主,更多是因为中老年人在行动上相对会慢一些,饮食上也有更多特殊要求,所以早期的区分主要是基于功能性的,他们和年轻人、中年人有本质的不同。
但现在严格来讲,区别更多是在文化层面上——尤其是如今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出生的这批“新活力老人”陆续退休,他们已成为市场消费主力,和50年代的人完全不一样。
首先,他们既看重功能需求,也更强调文化体验和在地生活,这是产品内容上的根本变化。另外在出游方式上,他们和年轻人一样追求自由:一方面自驾越来越多,另一方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三四十人的大团,而是逐渐小团化。他们往往因兴趣、职业、同学、战友等小圈层聚在一起,讲究的是同龄、同兴趣、同经历,团规模都不大。其实这对我们现在做中老年旅游提出了全新的挑战。
许义:您提到的这点我非常认同。其实我在2020年《新旅游》那本书里就提出过“新老年人”这个概念——他们确实和过去我们理解的中老年旅游方式完全不同,无论是体验还是需求都发生了根本变化。所以您刚才说的“以青年人的方式做老年旅游”,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到位,确实就是这么个方向。
徐华玉:确实,现在这批新退休的中老年人,是享受改革开放红利最充分的一代。他们成长于热情似火的年代,至今仍保持着那份活力。所以我们为他们提供服务,一定要年轻化、时尚化。
他们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服老,并不觉得自己老了,只是到了规定年龄,尤其在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企这些地方,不得不退下来。但从身体、精力各方面来看,他们完全没问题。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,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,子女也接班了,也愿意主动退下来。因此在服务方式上,必须有根本性的变化,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比如现在还有旅行社纳闷:中老年人都去哪了?怎么不来了?如果还沿用过去送鸡蛋、送大米、送油那套方式,那就太low了。
作为目的地文旅集团,如何适应新旅游时代的经营变化?怎么保持这样一个规模企业的持续竞争力?
徐华玉:我想创新主要来自两方面:一个是经营上的创新,另一个是管理上的创新。
当然,对很多小企业或创客来说,可能90%的精力要放在经营上,管理占10%,只要做好自我管理就够了。但做到一定规模之后,这两者就都必不可少。
经营上的创新,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同品牌那样,总的来说:第一,产品一定要模块化、可拆卸,像乐高一样;同时内容上要加强体验感,让游客不是局外人,而是能参与进来,有真正的参与感。
第二,服务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。过去传统旅行社最大的问题是太“刚”了——线路固定、吃饭固定、服务固定、价格固定,客人没有自由度。所以我们服务上要给客人更多选择。
但要实现这些,公司组织也得相应调整,必须建立柔性的组织架构。也就是说,我们中后台要能把服务或支持做成可拆卸的模块,通过平台赋能给前台,由前台组装后提供给游客。如果中后台不赋能,只靠前台自己去创新,成本高、效率低,效果肯定不好。所以推行“平台+创客”的组织变革,本质上是为了适应业务和市场需求的变化。
我个人认为,这种模式是未来创客走向规模化的必经之路——当然这只是我这些年的体会,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。而且现在有了数字技术的支持,我们完全可以做到。过去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,信息都是孤岛,没法实现这种协同。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分散化经营,让每个小团队专注一个细分领域,像工匠一样做精做透。但和过去手工作坊唯一的区别是:现在他们在一个平台上,可以得到赋能,做二次开发。
未来3年,安徽环球文旅有什么样的大概的规划?
徐华玉:我想未来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抓:
第一,经营上还是要重点抓住C端客户,这是旅行社的命根子,尤其想做品牌企业的话。很多企业大起大落,就是光靠政策吃饭——政策红利来了就起来,没了就不行。过去可以这样,但真正想做持续、做百年企业,必须靠满足基本需求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、保证不亏损。在这个基础上,如果再有好的项目或政策红利,公司就能健康盈利,这两者缺一不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抓好C端,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,都要服务好。
第二,就是重点抓“两头”:一个是孩子,一个是中老年人。这两个群体特别需要服务——年轻人可以穷游、睡帐篷,但孩子和老人不一样,他们需要更多照顾和提升,服务难度大,但也更有价值。
第三,是服务好那些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人群。他们的时间成本很高,我们本质上是用我们的时间换取他们的财富,因为他们单位时间创造的收益比我们高得多,这是一种价值交换。
第四,是做更多主题性活动。比如为中老年人设计文化艺术交流与旅游融合的项目,还有体育+旅游——像我们在安徽做的马拉松旅游融合,未来还会拓展到更多“旅游+”领域:文化+旅游、体育+旅游、农业+旅游、教育+旅游……这都是未来的重点方向。
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是深耕安徽旅游目的地。我们要挖掘当地最有特色、甚至网络上查不到的独特资源,尽管这些资源非标、有风险,但我们就是要整合在地文化、在地生活,形成独特体验,做好目的地服务。这个板块不仅要吸引国内游客,还要吸引更多入境游客来安徽。
您在旅游行业从业接近40年,这40年什么变了?什么没变?
徐华玉:这方面变化真的很大。以我这40年为界来看,40年前是从计划经济慢慢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——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是固定的,你按部就班做就行;到了市场经济初期,还属于短缺经济,只要有产品就不愁卖,本质是让客人去适应产品。
而40年后的今天,最大的变化是一切产品和服务必须去适应用户和客户。这个看似简单的顺序调换,其实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:我们的认知、运作模式、组织架构都要调整。就像我前面说的,原来企业是金字塔结构,现在要变成倒金字塔,把一线部门、离客户最近的岗位推到最前面,所有力量都服务于他们。以前是资源为王、产品为王,现在必须用户为王。
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“40年的新兵”——真得重新学习。如果还想在旅游行业继续做,就必须以小学生的心态重新熟悉市场,去懂客户、洞察需求,再一步步用产品和服务去满足。
这个“新兵”体会也体现在管理上:过去短缺时代,用命令式管员工也许还行;现在的员工不仅要工资待遇,还要情绪关怀和个人发展,三者都得兼顾。我们要让员工有好的待遇,更要在工作中找到意义感、激发内驱力。这些无论经营还是管理,都是本质的变化。
最近在关注和思考哪些关于企业经营的问题?
徐华玉:我们企业其实一直在持续变革。今年从9月份开始,公司就已经启动了对2025、2026年,甚至展望到2028年的三年旅游规划。
首先,我们把2017年以来陆续推进的各项调整做了系统梳理,形成了一份企业发展战略大纲。在这个大纲之下,我们制定了三类行为规范——高级管理人员、决策层和员工各有相应的准则。目的是让大家从理念到行为,都能跟上这个新时代的要求。
其次,在组织架构上,像我前面介绍的,也做了调整:把原来前、后台两台结构,细分为前、中、后台三层。
第三,在架构调整之后,今年我们在人员上也做了较大变动。我们提前明确了公司明年的目标、各部门的业务与职责范围,以及对应的任职资格,然后让所有管理层原职务全部免去,重新选聘上岗。选聘有两种方式:如果组织没变,且原岗位业绩达标,可以通过述职留任;如果组织已调整,或有人来挑战这个岗位,就采用竞聘方式重新选人。这样我们真正选拔出了一批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人才队伍,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。这些就是我们为2026年乃至更远未来所做的一系列准备。
在这40年波澜壮阔的旅游事业中,有什么对你来说重要的进化时刻?
徐华玉:我想人的进化是建立在一步步进步的基础上的。对我个人来说,人生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。
我是1985年从上海旅专毕业的,从那时到2000年,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教学上。当老师期间,我至少上了十几门不同的课,这为我打下了理解这个行业的功底——虽然谈不上多深的理论基础,但对行业的认知比一般人更全面、更深入一些。
2000年之后,尤其是2003年开始创业,我逐渐把过去的积累和旅游实践结合起来,这才对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可以说,2000年之前是打理论基础的阶段,那时候安徽的老旅游人里,百分之七八十都听过我的课。而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,是在创业中真正理解行业的阶段,很多东西过去讲课是理解不透的,那之后才从“概念到概念”变成了“从实践到理解”,学生也更爱听了。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万达并购我们之后,一直到2019年,那是我个人在管理上成长最快的时期。打个比方,过去我们很多创业者的管理像是“砖混结构”,靠经验一点点堆起来,没有系统架构。
到了2013年,公司规模过亿,需要重新搭建体系,万达进来就像是把我的“砖混结构”拆了,换成了“框架结构”。管理模式完全变了:过去是“以人定事”,有多少人做多少事;现在是“以目标定事”,围绕目标去选人、做事。这是我在管理上的一次真正进化。
疫情之后,对我而言完全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无论是经营还是管理,我都像是重新回到“小学生”的状态,把自己清空,忘了过去。我在学校跟年轻学生讲,现在确实是年轻人的时代。如果在十年前,你想超越我们这代人很难,因为那是个确定性的年代,靠的是经验;而现在是不确定的年代,靠的是创新思维。我们这代人在思维的活跃度上,已经没法跟年轻人比了。更何况,我们要想接受新事物,还得先把脑子里的旧东西清空,这需要成本、决心和时间。所以我说,现在反而是年轻人最好的时代,而我们必须重新开始。慢慢地,我也开始找到一些新的感觉了。
对于环球文旅集团和整个旅游行业,我始终充满信心。
眼下的困难不是行业没有希望,而是我们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,甚至可能被时代抛弃了——但不是被行业抛弃。关键是我们没有进化,没有跟上这个时代。我常说,没有时代的企业家,只有企业家的时代。
我们怎样一步步跟上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依然充满激情。我特别希望能找到一条相对确定、能稳定走三五年的路,然后彻底退出,把班交给年富力强的年轻人。